榫卯里的父亲
袁俊
清明过后,老屋里的霉味总带着几分松木的清苦。我蹲在父亲的木工箱前,铜锁扣上结着薄锈,轻轻一拧,“咔嗒”声里漫出半世纪前的木屑香——那是父亲的气味,混合着墨斗线的棉麻味、刨花的辛香,以及老茧擦过木纹的温热。
父亲在十里八乡被唤作“袁木匠”。他的手艺是祖父用柳条抽出来的——十二岁起,每天天不亮就得在厢房里拉锯,锯齿啃进松木的“吱呀”声里,混着祖父的呵斥:“榫头要吃三分,卯眼得留七分,做人跟做活一个理。”父亲的右手食指永远微蜷,那是十七岁时被凿子穿透的纪念,伤口愈合后凹成月牙状,敲钉子时却比墨线还准。
七十年代初,公社书记看中父亲的手艺,要调他去当“公家人”。母亲说,那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整包旱烟,火星在暮色里明灭,最后把烟蒂按进青砖缝里:“三十斤粮票养不活八张嘴,我这双手,还是拉锯来得实在。”于是他继续背着工具箱走村串户,箱底藏着个蓝布包,里面是六个儿女的学费单,边角被汗水浸得发毛。
父亲的木工箱里永远躺着十八件家伙:青铜墨斗吸饱了松烟,锯齿上凝着暗红的树脂,刨刀被磨得映得出人影。他常说:“木匠的家伙比老婆亲,你看这斧头,握得越久越有灵性。”每次给新人打婚床,他总要在床脚刻朵小牡丹,用凿子敲出“百年好合”的暗纹,说是“给木头里的魂儿听的”。有次我摸黑起夜,看见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父亲正就着这点光给邻村姑娘修梳头匣,凿刀在象牙雕件上簌簌落屑,像在给月光动手术。
他最盼的是有人接他的班。儿女里唯有我对墨线感兴趣。十六岁那年暑假,他把祖传的“龙头锯”塞给我:“先学破料,锯路要直,心也要直。”松木在锯齿下裂开金黄的纹路,树汁溅在袖口上,凝成琥珀色的疤。某天黄昏,斧头突然打滑,食指肚顿时绽开血花,父亲冲过来时,我看见他眼里闪过疼惜与释然。他用嘴吸净伤口的木屑,从围裙上扯下布条包扎:“你啊,还是拿笔杆子合适。”
1987年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正在后院劈柴。他用袖子擦了擦手,把通知书举到檐下看了又看,晒得黝黑的脸膛泛着红,最后从木箱底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他攒了三年的粮票,叠得方方正正,边角用棉线缝过。那晚他破例喝了点酒,指着墙上的工具架:“这些老伙计,以后就陪我养老咯。”
后来我每次回家,总看见他坐在门槛上打磨工具。生锈的斧头在油石上转出火星,刨刀刮过旧木板,卷出薄如蝉翼的刨花。他不再提让谁学手艺,只是偶尔轻拍我的肩:“你们读好书,比啥都强。”
父亲走的那年,木箱里的墨线已经发硬,锯条上结着蛛网。我把他的工具一件件擦净,突然在刨花堆里发现片泛黄的纸——是我当年的木工笔记,歪歪扭扭写着“鲁班尺用法”,旁边有父亲用铅笔批的:“尺短寸长,心正才是尺。”
如今我在书桌前写字,偶尔会听见木屑簌簌掉落的声响,像父亲当年在隔壁厢房做活。那些未能传承的榫卯技艺,早已化作更坚韧的血脉——他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如何让木头听话,而是怎样让自己成为一块端方的料,在生活的斧凿下,开出经得起岁月推敲的卯眼。
窗外的泡桐又落了花,我摸出父亲的墨斗,往棉线上滴了滴松节油。拉出线绳的瞬间,仿佛看见他眯起眼,将墨线绷在两块木料之间,轻轻一弹,便在时光的木板上,留下一道永不褪色的直线。
编辑:但堂丹
相关新闻
-
咸宁市举办首届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展示活动 传承弘扬劳动美 技...
咸宁网讯记者刘震、见习记者张克鼎报道:番茄鸡蛋在快速翻炒后香气满满地出锅,木料刨花在几分钟内簌簌落满一地,布料在快速...
-
那只松木箱
张冲(赤壁)那只泛着黄漆的松木箱放在我家顶楼的杂物室,如今已经很陈旧了,但是用湿抹布用心地一抹,看上去还是有新的成色...
-
铭记叔叔
聂松彬(赤壁)叔叔叫永典,小名水仙,是我父亲唯一的弟弟。望着叔叔手里的手枪,我迫不及待地跳着要玩,但叔叔总是诡秘地一...
-
咸宁市召开推进会调度督办斧头湖水环境治理工作

咸宁网讯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姜明助报道:26日,我市召开推进会,专题调度督办斧头湖水环境治理工作。王远鹤指出,斧头湖是我省...
-
杜新国陪同调研斧头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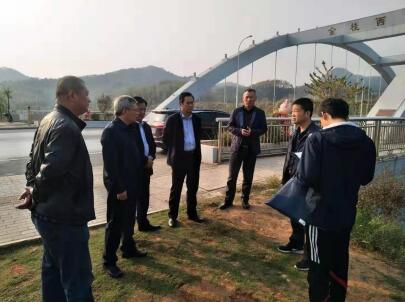
11月8日,省生态环境督察办郑国安带队一行6赴咸安区对斧头湖项目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调研督办。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察看...
-
斧头湖陈七嘴生态修复项目竣工验收
11月13日,湖北省斧头湖管理局组织咸安区纪委、财政局、水利和湖泊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咸安分局、咸宁向阳湖湿地管理...
-
饮水源头水清岸绿,斧头湖上鱼跃鸟飞!全域联动,精心绘制水...
澄澈的斧头湖已成为我市水生态保护一道风景线“一条小河潺潺流过,一朵浪花一个传说。针对马桥水源地保护区而开展的各类工作,...
-
副市长谭海华深入调研斧头湖生态修复工作

11月22日,咸宁市副市长谭海华带队调研斧头湖生态修复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大项目投资办主任孙道远、湖北省斧头湖管理局...
-
省生态环境厅调研组赴嘉鱼调研斧头湖治理工作
5月27日,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国斌,省生态环境厅驻鄂南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徐松一行赴嘉鱼调研斧头湖治理工作。调研...
-
防汛备汛早行动 嘉鱼东湖围堤加固工程完工

咸宁网讯通讯员雷平、龙琳报道:近日,嘉鱼斧头湖东湖围堤加固工程全线完工,大堤完成加高、加宽、披绿工作,涵闸、泵站焕然...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咸宁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咸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咸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咸宁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娱乐新闻
-
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风雪夜归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滤镜 《黄雀》讲述充满“锅气”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






















